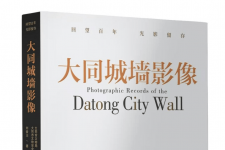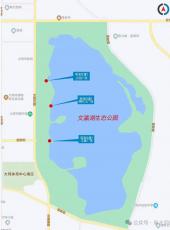霍俊明,河北丰润人,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诗集、理论著作等十余部,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后天”双年奖批评奖、《星星》年度批评家等。
张二棍,山西代县人,一个内心忐忑面相庄严的不优雅青年。
霍俊明:
二棍兄(王单单在写给你的诗里半严肃半玩笑地称你为“棍君”),作为首都师大第十三位驻校诗人,作为诗刊社的兼职编辑,还是谈谈一年多来在北京的感受吧!
张二棍:
谢谢霍老师,十分高兴能用文字的方式,与兄来一场赏心悦目的畅谈,恰如夏日午后有友来访的惬意,没想到你还带着一盒精美的点心,美哉。
回顾自己这一年多的时光。驻校诗人和兼职编辑这两种临时身份,都与诗有关,甚至背负了一点儿小小的责任与使命。“驻校诗人”,不是简单的“住校”,更不能“蛀校”,要一边与前辈们求索,一边与后生们分享,要坚持创作更要时刻反省自己的创作。而“兼职编辑”的要点,则是“兼”这个字,兼听、兼容、兼济天下,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兼职也需专心,临时更要恒思,所以这一年我都在努力去掉“兼职”这二字的副作用,努力让自己显得一本正经又专又红,可能让大家失望了,抱歉啊。我这样一个野诗人,突然从散养变为圈养,突然从天马行空的地质队员变成斟词酌句的兼职编辑,突然从一个上学时候都逃学的劣币,变成一个在讲台上一二三四地与学生们分享诗歌的金光闪闪的张诗人。这三个转变,就像万恶的三座大山啊,让我明白了自己在学问和诗歌面前的“矮矬穷”,唉,谢谢大家的担待吧。现在这个无知而有畏的张二棍驻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敲锣打鼓吧。
霍俊明:
很多人看到你名字的时候都会感受到某种兴奋、诧异和戏剧性,而极其接地气的“二棍”又曾经是极其民间和乡土化的称呼,在我早年的老家,叫二棍、二蛋、二狗、二傻、二头的非常多。每次想到“二棍”,我就仿佛回到了早年的乡下,仿佛你就是村里隔壁的那个蹲在墙角抽烟的玩伴。由你的名字、你的诗歌、你的精神背景,自然会联系到你的老家代县,联系到你现实和诗歌中的家乡和亲人,谈谈他们吧!在一个乡愁式微的年代,谈论他们也许并不轻松。你同意别人所说的你诗歌中存在着“乡愁”吗?你认可一些评论者说你是“新乡土写作”的代表吗?
张二棍:
兄,欢迎你跟随“张二棍”回到乡下,回到童年,这里是你的“还乡河”,我们一起来练一套你的霍家拳吧(据悉,你苦练三年霍家拳,某天,被低年级晚辈一招覆灭,自此兄弃武从文,终有所小成)
名可名,非常名,给自己一个奋不顾身的笔名,其实就是往自己脸上涂抹一些大红大绿的油彩,让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暂时游离那个既成事实的肉身的“张常春”,去开辟或者塑造一个也许永不可能存在的幻境中的“张二棍”。大家对于“张二棍”的兴奋,诧异可能是源于“张二棍”与“诗人”之间的割裂和悖谬。是的,这个“张二棍”恰恰也是我的诗观的表现。如果以古诗的审美来看,现代诗主动背弃了结构与音韵,独自找寻反诗意的诗意,这多像“张二棍”啊,没有“江梅伴幽独”的高冷,也不具“吴钩霜月明”“的侠气。“张二棍”也是反诗意的……
关于乡愁,兄说的很对,这确实是一个乡愁坍塌的年代,许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农耕文明的乡村,早已消耗了或者变异了。而人口的迁徙,通讯的发达,交通的快捷,也让“乡愁”越来越显得矫揉和陌生。但我们的愁并不会减少,我们的乡愁转移了,变异了,乡愁里的乡变得更加微妙和不可言说,也许乡愁阔大成了县愁,省愁,星球之愁,也许乡愁萎缩成了对一间旧房子,一个土瓷碗的房愁,碗愁。但愁仍然砥砺着也折磨着我们,每个人都是寻觅归宿的游子啊。至于那些乡亲们,现在因为篇幅所限就不说了,他们存在着,幸福着,无奈着……而我的写作,从来都是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还不配“新乡土写作代表”这几个滚烫的字眼,我会努力。顺便想提一下,我心中真正的新乡土写作的代表,他们是集市上说顺口溜的卖货郎,葬礼上一声声把自己唱哭的哭丧人……是他们的声音,还响彻在那一片片大地上,是他们用最质朴的语言,为乡土保留着最后的元音。
霍俊明:
顺便谈谈你的胞弟张常美吧!他的性格和他的诗歌和你有区别吗?
张二棍:
这个“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名字背后,也暗藏着一个和我近似的人。长着同一幅吓死古人不偿命的面孔,被同一个平凡的母亲拉扯大,接受同一个父亲的拳打脚踢与耳提面命,念同一所已经衰败的小学、中学,我俩天天撞衫,撞到连补丁的位置都几乎一样,我俩在同一个地质队……算了,不举例了。说说他的诗歌吧,就像一个人呵斥或者训诫自己的影子一样,我怎么忍心说他诗歌的坏话呢,可也不能因为我俩挺熟,就盲目赞美。我始终认为性格与胸襟,决定着一个诗人的作品姿态和写作方向。他的诗歌,空灵一点,轻盈一点,薄一点,脆一点。
霍俊明:
你18岁就进入了地质队,当了一名钻工,你却在工作十年之后,也就是28岁时才开始写诗。那么,在18到28岁之间,你经历了什么?这段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钻工张常春”与“诗人张二棍”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或者说生活和写作存在着怎样的共振或龃龉的关系?最初第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境下写出来的?为什么选择了诗而不是其他文体?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吗?一个人和自己争辩,产生的往往是诗。你的内心里是不是存在着一个与现实中不同的另一个“张二棍”?
张二棍:
十年弹指一挥,十年荒野行走,十年孤灯阅读,十年风餐露宿 。这十年,我看到了最底层的良善和幸福,也目睹了他们的挣扎与污浊。我见过三个被贩卖的缅甸少女,困在晋冀交界的山村里,相互梳着头,鬓角插着采来的野花,那一刻她们是幸福的;我见过一个将死之人,跪在田埂上,捉住几只奇怪的虫子就往嘴里塞,他相信这偏方里的神虫能让他活下去,那一刻他是满怀憧憬的;我见过一对困厄的夫妻,扭打在一起,满脸血迹,最后又抱头痛哭,那一刻他们是悲壮的;我在山顶上见过一个老迈的牧羊人在风雪中行走,深一脚浅一脚去寻找他丢失的小羊,他和我说起他一生都没有吃过鱼虾的时候,那一刻他多么无助……
我曾长久经历着这一切,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像极了一根根稻草,往一个叫做“张常春”的人身上压迫着,我越来越重越来越害怕,我希望寻找到一个“张二棍”和我一起来背负这些要命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张二棍”能够用字句把这些稻草运送到纸上,这样我会轻松一些……
因此,在某天,我开始了自己的记录,起初是一些小散文,小日记。再后来,我把这些文字分行,这大概就是诗了。
霍俊明:
我知道你是天蝎座,对星座和性格、命运的关系,你怎么看?每个人都会累积自己的精神肖像。每次看到微信和刊物上你的照片(大多都是黑白色的)我就会有同样异样(包括亲近)的感觉,形象上的特异反倒是刺激了阅读者的口味,“1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记者见到了这位自称只会‘爬大山、喝烈酒、写破诗’的‘80后’诗人。‘看到二棍的照片被逗乐了,怎么会有被晒得这么黑的诗人?’有粉丝在网上打趣道。站在记者面前的张二棍,肤黑眼细,恰如他的名字一样接地气。”记得张执浩曾这样评价过你——“这位有着‘异人’面相的年轻写作者也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资禀赋”。此时,我想到一段余秀华评价你的话,“唉,怎么说呢,说外貌和才华成反比吧,好像打了自己的耳光,说外貌和才华成正比吧,肯定打了张二棍的耳光。”余秀华甚至还开玩笑地说你和她是诗坛的“绝代双骄”。
张二棍:
哈哈,当一个人的长相被无数次挑剔,只能说明此人除了面孔之外已无其它任何缺憾了吧。这个人肯定灵魂饱满,人格健美,万事俱备只欠窈窕了。而我恰恰是那个被无数次挑剔过的,我骄傲了吗?霍兄,我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盼望自己长得多好了,我害怕别人嫉妒。
说到星座啊手相啊生辰八字,我几乎都是不相信的。但我深深知道,有一种冥冥中的东西,一直如影随行,默默加持着或者改变着我们。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的这条命,其实从来都是在懵懂和混浊中独行。当我们回首,往事并不是“悠悠”的样子,我们的记忆中永不会存在有一条线或者一个面,它是一个一个小点串起来的。我们五岁,十岁,二十岁,到头来都只会剩下某一天的某一件事的某一个瞬间,比如我清楚记得某个黄昏中,我和弟弟坐在门洞下等着母亲归来,远远望见母亲的衣衫被秋风吹动的样子,我忘了后来的母亲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饭,甚至望了她当时的样子,她手里拎着什么……我只记得那衣衫被秋风吹着,远远的被秋风吹着。所以,我们活着,活在一件件小事的一个个节点里,我们的命运被这些小点改变着,修饰着,支撑着。也许一次浅浅的阅读,一次深深的交谈,一只蝴蝶在雨中的窗台上垂死的模样,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点,会改变我们的一生吧。
霍俊明:
你的诗歌中一部分处理了乡村、底层和苦难现实,那么,当有媒体和评论者称你为“中国诗人底层写作的传奇”“在生活的深渊中写作”“以诗歌的方式拆迁底层的苦难与疼痛”“用诗歌记录卑微”,你是什么感觉?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所谓底层的问题、伦理写作(比如题材和主题的社会性、阶层性和伦理化,痛感写作、苦难叙事等)和写作伦理(写作的功能,为什么写作,写作者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关系)问题?诗选集以及纪录片《我的诗篇》中着力突出了我们时代诗歌写作者的社会和阶层身份,那么,你觉得社会身份和写作之间存在着什么本质关联吗?
张二棍:
霍兄列举出的那些引号里的话,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毫无意义。那是“他言”,而我需要“自证”。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应该不断主动放弃自己的身份,名誉,过往的作品。一首诗一旦写成,它就是一条独立的生命了,在每个阅读者那里,它拥有了自己的呼吸、心跳、腔调,它已经背弃了作者。所以我认为,“底层”、“深渊”、“苦难”、“卑微”可能是某些诗歌的要义,而不是写作者的符号。我也可以写天使、殿堂、发动机、大学。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生活在山野中太久,睁眼闭眼就是穷乡,野店,泥泞小径,所以我写了一批那样的东西。就像兄提到的《我的诗篇》,我不关心是谁在写下那些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作品写了什么,写的如何。诗歌说到底,不必附加什么题材、流派、年代、区域,只有好或者坏。霍兄,我是不是又跑题了?
霍俊明:
自然、旷野,在你的诗歌空间中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它们在你的语言和精神内部意味着什么?我的阅读印象里,你的诗歌姿态很多都是俯身向下的。2017年5月,刘年和你骑马向北,“打算耗时一月,从林西县,经东乌珠穆沁旗、阿尔山、呼伦贝尔,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未必成功,但已成行。”你和刘年骑着马的内蒙古之行,成了这个时代的特例和反证。这肯定不是一个骑士的时代,我想到的倒是与风车大战的孤独骑士堂•吉诃德。这次行走是怎么产生的?对你以及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
张二棍:
也许是在野地里徘徊太久了,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旷野这个词,就能够很具象、很迅捷地出现一个个画面。初春的,深秋的,寒冬的,什么花摇曳在什么树下,什么鸟在我身后怎样叫着,山泉穿过什么形状的乱石,大蘑菇在腐烂而小蘑菇在生长……我诗歌中的旷野,是众多荒野的集结,是相对于城市、大厦、铁轨的亘古,是诸多生命平静的等待,无数场风雪浩大的掩埋,是一头山猪与另一头山猪欢愉的婚床,是一条毒蛇迅疾地分开草丛返回巢穴,而蛇蜕在风中无助地晃动。因此,我常常觉得,旷野中的万物,过着比我们精彩一万倍的生活,旷野中也有温情、秩序、抚慰、号令、推诿……当我懂得这一切,我怎么会趾高气扬,怎么会不卑微、不俯身啊。和刘年老师的骑行,是兴之所至,是几句简单的沟通。走不走?走!啥时候?明天或者后天!去哪里?出发前再说!怎么走?有马骑马,无马骑驴!其实诗人的行动,就应该这么简单嘛。
霍俊明:
你的诗总是给人隐忍和悲悯的感觉,觉得你的精神承受能力很强大。这是性格使然,还是你认识世界乃至诗歌话语方式?
张二棍:
想通了,就能承受一些东西。想不通,一个白眼就会毙命。庄子说过,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这就告诫我们,一个人的欲望和他内心的承受力是成反比的。君不见,亿万富翁一旦投资失败变成百万,他就觉得穷苦不堪,就要跳楼,多傻啊;君不见,一个高官一旦失权就要服毒,多傻啊;君不见,诗坛来来往往,一些人为了发表为了得奖,弄了多少笑话。如果每个人记得自己的本初心,那么我们每一天的写作,就会是一场胜利,我们也会获得无数幸福。我希望获得那幸福……
霍俊明:
我曾看到一个有些偏激的看法,把诗人分为西方派和本土派。你的诗受到过西方诗歌的什么影响吗?或者说在你的阅读中是否喜欢过一些异域诗人?
张二棍:
现代诗肯定绕不开西方,我阅读的西方诗歌并不少。但作为一个读不懂原文的人,不可能逐字逐句去研读被动过手脚的经典。我更乐意看看它们的结构,情绪等等。我喜欢的国外诗人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大师,不在我的阅读范围里。以后有空,慢慢读吧。具体说到影响,我估计我自己是看不出来的。要不,兄帮我看看我有没有被潜移默化过?
霍俊明:
以前你的诗几乎都是短诗,近期写了一些较长的诗,比如《敖汉牧场•羔羊•雪》《山野书》。这是出于何种考虑?你觉得写了十年之后(写作往往容易出现惯性),自己的诗歌到了什么一个阶段?现在的困惑在哪里?
张二棍:
年轻的时候,身上会有暴烈之气,想着速战速决。喜欢咔嚓一声,不喜欢叮叮咚咚。其实这一直也是我个人的局限,我无法把诗歌写得绵延、浩瀚、悠长。而近期的几个小长诗,说到底也是短诗披着长诗的外衣,我不过是让它们在行文之间,互相关照一下,推动一下。写作时间已经不长不短了,在十年这个节点,困惑会越来越多。我也反省过总结自己的问题,比如有技而无巧、象动而意滞、情郁而词浮等等,无法解决。只能留给时间,用写作去推动写作吧。
霍俊明:
近期你诗歌的“元诗”倾向逐渐突显,比如《元神》《徒留<衣冠冢>》《我不能反对的比喻》《对一首诗歌的统计学》等。这是一个诗人文体自觉能力的强化。实际上,很多重要的诗人都写过这种以诗论诗的元诗。这涉及到一个人的诗歌观念和文体意识。那么谈谈你对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吧!
张二棍:
当我无法完成一首作品,或者说内心想要的诗歌和业已成形的诗歌之间,总有深深的鸿沟与敌意。每当这些时候,我就去写点东西,对自己鄙视一下,或者提醒一下。我把它们分行,相当于切割一下自己,就有了兄说的那些元诗歌。
霍俊明:
你和刘年、王单单无论是私交还是诗歌阅读上,彼此认识都很深。比如刘年写给你的《致张二棍》:“都喜欢远离人群,都喜欢低头的稻穗 / 我乐水,你乐山 // 在南溪,我水獭一样翻滚的时候 / 你白眼青天,蹲在石头上 / 像八大山人画的一只苦斑鸡 // 北京又下雪了 / 覆盖了皇宫,想必也覆盖了你深山的帐篷”。王单单则给你写了一首长篇献诗《闲话诗,兼与二棍书》。谈谈你对他们两个诗歌的印象吧(可以说的狠一点,哈哈)!王单单在写给你的献诗中有一节谈到了你诗歌的特点(诗歌与传统和现实的复杂关系)以及潜在的危险(“棍君作《五月的河流》,传统的比兴 / 对于诗意的维护,仍然牢固、可靠”“短句的优势,在于瞬间凝聚起 / 抒情的力量,短促急切的节奏 / 暴风骤雨般,将个人情感 / 推至喷涌状态,但也容易 / 陷入模式化的泥淖,二棍啊 / 你要警惕!”)你认同吗?
张二棍:
有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如果反过来想,是我族类,其心不异。此二人产于僻壤,长于柴扉,久居人下,未丧其志。做为自己心里认可的兄弟,真的欣喜他们对写作的态度。刘年勤奋、踏实,憨厚的外表遮掩不住半颗动荡不安+半颗随遇而安的内心。所以他的诗歌,大多语焉不详,三言两语之后就戛然而止,仿佛他只是个跑腿的邮差,只负责把一个简短的电报送来一些微言,留给我们去体悟那些辛酸苦辣。而王单单勤奋、踏实,继续憨厚的外表掩盖不住……昂,这组词汇形容过刘年了。重来哈,而王单单,有着傲人的心气与发型,不拘小节又深明大义。他的作品,时而壮烈如夕阳,时而勇猛似死士。他有一种打破砂锅还在锤击不已的刨坟精神,写诗步步紧逼,所以读他的诗,有黑云压城的感觉,这就是诗歌所谓的力量吧。今天就夸他们这么一点点吧,不能夸太狠了,要不然他们会让我喊老师的。批评的话更不说了,大家还要相见,留待酒过三巡,我好脱口而出。刘年和单单,我,其实私下里经常展开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的。当然,我们的批评是三言两语读后感式的。假如有一天,我们的修养能够与霍兄比翼齐飞,大家再来一场详尽的地毯式的询问与质疑。
霍俊明:
我越来越发现当下我们的诗歌现场,存在着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即很多诗人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却没有一首代表作。我觉得,你肯定有代表作,因为很多人对你几首诗谈论的频率非常高(比如《石匠》《穿墙术》《在乡下,神是朴素的》《旷野》)。如果让你列举最认可的你个人的几首诗,它们是哪几首?(千万不要说我还没有写出好诗,好诗在以后啊,哈哈)
张二棍:
连霍兄这么挑剔的批评家都觉得有了,那我岂能妄自菲薄。可我还是觉得,代表作不是自己说了算,还需要读者经过长期的肯定和赞许,产生相对广泛的影响。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其实也和大姐大嫂们谈论的那些差不多。当然,如果我此刻脸皮厚一点,我完全可以再举出《静夜思》,《水库的表述》,《某山某寺》,《黑夜了,我们还坐在铁路桥下》,《我用一生在梦里造船》,《太阳落山了》,《默》等等一些自己满意的,但我能说么?我不可自吹啊,所以我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好诗在以后!
霍俊明:
有时候写诗会有虚无的感觉,尤其是在人生变动的转捩时刻。我们的对话就此打住吧,山高水长,希望日后可期,再次饮酒相聚!
张二棍:
诺!
2018年7月,北京
——原载《诗歌月刊》2018年9期
返回新大同,查看更多 本文地址:霍俊明VS张二棍——一个很阔气的访谈https://www.sxdt.com.cn/show-14-17127-1.html